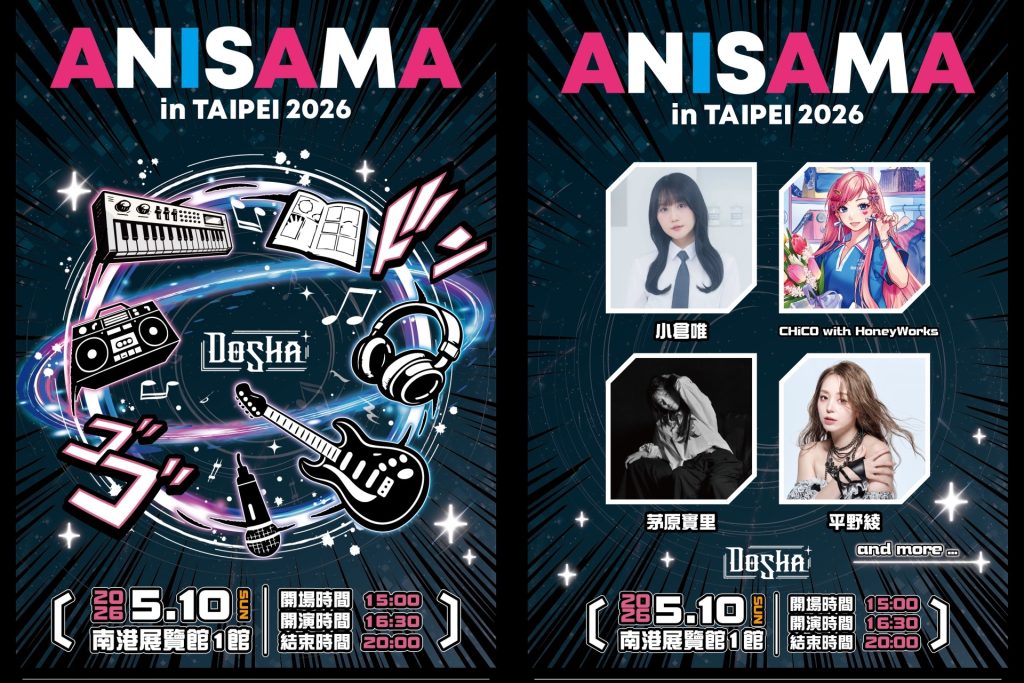日本鬼才影像創作者關根光才繼首作《我,為愛而活》後推出第二部劇情長片《難言之隱》,由全方位女星杏擔任主角,於 11 月 22 日正式在台上映。本片故事改編自北國浩二所撰寫之原著小說《謊言》,探討兒虐以及失智症議題。關根光才導演過去曾以短片作品《天時地利 》出道榮獲紐約短片影展最佳外語片殊榮,隔年獲頒坎城國際創意節青年導演大獎。 2008 年開始與國內多名音樂人、藝術家合作,推出多部 MV 及廣告短片,包括 Mr.Children〈 足音~Be Strong〉和 The fin. 〈Night Time 〉、〈Shedding〉…都由他執導而受到高度矚目。除了電影之外,也積極參與反戰、反核、難民等議題的藝術行動。隨著《難言之隱 》在 11 月初金馬影展台灣首映,關根光才導演也隨片訪台會影迷。趁著導演來台之際,迷迷音特別與導演進行對談,聊聊這部片與他的電影哲學。
延伸閱讀:專訪 / 關根光才談《難言之隱》:「謊言」真的完全是壞的嗎?(有雷)
===以下有雷===
ー深陷過去之中走不出來的人大概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會美化過去的痛苦,有些人則會深刻記得痛苦。好奇導演自身是什麼樣類型的人呢?
老實說我覺得兩者都有。比如說這個故事是基於我祖父罹患失智症的經驗,當時的確很痛苦,但我非常愛我的祖父,所以雖然有辛苦的回憶,也可能會把這段回憶美化,與其說是美化,應該是因為發生過這些事,最終我更能接納我的祖父,感覺能夠理解他。過去發生的這些事並不只有痛苦,對我來說不是只有負面的感覺,這不僅僅是面對我祖父罹患失智症的事情,我對很多事情也有這樣的看法。我是那種會認為所有發生過的事都有其意義的類型。
ー生病這件事情病患是最辛苦的,不過由於認知症有許多人都會認為病人或許已經不記得,因而會偏向關注陪伴者的內心,但這部片中特別點出病患的內心掙扎,讓人印象深刻。
當我看到這本原作的時候,不禁回想起我小時候的情況。當時關於認知症的研究還沒有那麼進展,而且當時人們並不是用「失智症」這個詞,而是用「癡呆」,是偏向負面的字,還帶有點「瘋狂」的意思,大家會用這詞來形容失智症患者。現在大家認為這樣的說法其實有歧視的意味,所以現在已經不太會用「癡呆」這個詞來形容失智症。當時整個社會對失智症的症狀了解並不多,當我讀這本書的時候,才意識到也或許失智症對我祖父反而可以帶來某種救贖。當時如果我知道這些,也許對我的祖父的照顧會有不同的方式,或許我能更溫柔一些。我們的社會正處於高齡化時代,無論是在日本還是台灣,將來會有越來越多的家庭面臨到這種情況。了解這些,對自己和家人來說,並不會吃虧,反而會有更多的幫助。
ー導演的第一部作品《我,為愛而活》探討關於憂鬱症,也幫助觀者從不同面向了解憂鬱症。導演平常就對這樣的議題特別關注嗎?
我自己對社會議題有相當高的關心,雖然我並不是專門想深入探討精神疾病或認知障礙之類的議題,只是剛好第一部是以憂鬱症為主題,而這部則剛好與失智症相關聯。我並不是刻意要去探討這些疾病本身,而是想了解處於這些狀況中的人,他們到底在想些什麼、處於什麼樣的心情,這樣的理解對我來說非常重要。如果大家能夠了解這些情況,或許社會會變得更懂得寬容、更溫柔一些。從這個角度來說,這樣的討論也能促進社會的進步。實際上每次電影製作完成後也經常會有相關討論,我想這正是電影創作的意義所在。電影不僅僅是要讓人享受,它還能引發思考、促進交流,我非常重視這一點。
ー片尾曲〈tears 〉唱到「你認為什麼樣的未來是美麗的呢」,當初如何與羊文學溝通片尾曲的部分?
我並沒有給予太多的提示。羊文學的音樂風格帶有很多搖滾元素,節奏也非常強烈,所以我原本有些擔心,會不會他們的風格不太符合我當初的想法。我有向她們詢問風格部分預計如何處理,聽了她們對於作品音樂走向的想法後,覺得很不錯,於是我決定讓她們去自由發揮,沒有多給予建議。歌詞也是完全來自她們的創作,我覺得這次她們做得非常好,超過了我的想像,真的創作出了非常棒的歌曲。這讓我非常驚訝,也十分感激她們的努力。
ー剛才提到羊文學的音樂風格比較強烈,好奇最初會選擇羊文學的理由為何?
我希望能加入女性觀點來闡述這部作品,尤其電影本身的議題很深刻沉重,裡面不是老人就是小孩,所以希望可以加入一些年輕人的想法和能量。
ー導演過去曾與不少音樂人合作,好奇在配樂的部分是如何找到 Aska Matsumiya 來擔任?最近有沒有特別關注或常聽的音樂?
她住在美國,很久以前有一次她來日本的時候突然聯絡我,雖然我當時不認識她,但她說想見我,我們就見面聊了一下。那時她說她其實一直有意製作電影配樂,並且跟我談了很多對這方面的看法。之後,我也聽了她創作的一些音樂。從那時起,我就有考慮過未來有機會可以和她合作,同時也一直在想什麼時候會是最合適的時機。直到這次的電影,我想使用豎笛的音色來製作,而 Aska Matsumiya 本身有古典音樂背景,並且創作過許多電影原聲音樂,擅長使用古典樂器來創作現代風格的音樂,我覺得她非常適合,所以就決定請她來做配樂。
ー配樂的部分大概只有使用兩、三種樂器,跟這部電影的主要角色相呼應,這也是特別有意識來做的嗎?
樂器的使用大概只有三種左右,感覺上是真的非常簡單。這部電影的故事就是圍繞著這三個角色展開的,所以一開始其實元素非常少。雖然後來逐漸增加,但最主要的還是只有三個人。音樂方面則呼應故事發展,這三個人之間的同步感也變得越來越豐富。
ー過去曾為 Mr.Children 和 The fin. 拍攝 MV ,導演近期有關注或經常聆聽的音樂嗎?
Bendik Giske,是個實驗音樂的藝術家。他的音樂表現舉例來說,是一直在吹同樣的銅管樂器,比如小號或薩克斯風,但慢慢地打破音樂結構。我反而不太知道當前的流行歌曲是什麼,通常都是從孩子那裡聽了才知道「原來這是現在流行的歌啊!」。
ー這次來到台灣,在工作之餘,在台灣有什麼想要體驗的部分?
我來過台灣幾次,而且因為我的姐姐嫁給台灣人的關係,讓我對台灣有一定的了解,覺得是一個很放鬆的地方。其實來到台灣沒有特別想做的事情,光是走走看看,對我來說就很開心。單純只是在街上走走、拍些照片,就能讓我回憶起以前的感覺,可以好好讓腦袋放鬆。
ー那麼有什麼來台一定會做的事嗎?
會喝鹹豆漿,像這種把豆漿做成鹹粥的做法在日本是沒有的。
ー平常工作之餘會做些甚麼呢?
空閒時間大部分都在跟孩子玩,另外我也喜歡戶外活動,比如去露營、或者去海邊玩水。像韓國或台灣,現在戶外活動都很流行。或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被困在家裡的人們若不與大自然接觸的話,身心可能就會出問題,因此人們才會渴望接觸大自然吧。
ー這次電影中也有一段河邊露營場面,拍攝現場有甚麼有趣的事情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杏當時也有帶自己的親生孩子一起在河邊玩。現在杏搬到巴黎,對她來說,能夠和孩子一起體驗日本的自然,應該是很棒的吧。

ー電影拍攝大概花了多久時間?
大概是 18 天左右,不到三個星期。對於預算不多的日本電影來說,通常是得在兩、三個星期內拍完的。基本上每次都是這樣。至於劇本實際編寫,可能花了大約三年時間,從開始構思企劃到完成則是大約七年左右。這期間也有其他案子比較忙,所以很難集中時間快速完成,真的花了很多時間。
ー這過程中遇到疫情,好奇疫情是否對於劇本的編寫或是導演本身的想法有任何影響?
因為疫情的關係,拍攝預定大幅延期了,也正因如此,時間上變得非常緊湊。另一方面,我覺得疫情確實改變了我的心態。新冠疫情對人類來說,是一段非常痛苦的記憶,很多人都有過這樣的經歷。然而同時,我也覺得對某些人來說,這段時間讓大家意識到了一些重要的事情,這樣的時刻其實每個人都有可能經歷過。我覺得這樣的心情和記憶是應該好好保存下來的。所以,在那段時間,我也開始做一些繪本之類的創作,還有去露營。
ー疫情時否也有影響了導演的創作心態以及對於「電影」看法的改變?
經歷過疫情後,我的想法和作品的創作理念確實有些改變,雖然變化不算非常大,但我開始更加明白,無論是自己的人生還是每個人的人生,都是有限的,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並不是永恆不變的。我開始覺得,如果想要完成自己的人生目標,必須加快步伐,而不是一再拖延,否則就來不及了。
ー之後有其他想嘗試的題材嗎?
我想拍一部關於「原諒」的電影,想探討人們如何理解和原諒;事實上我現在正在進行的一個案子,某種程度上也是在探討這樣的主題。比如,戰爭這個問題,現在成為一個越來越巨大的挑戰。當我思考為什麼戰爭會爆發時,我覺得一個原因可能是人們覺得自己受到了攻擊、難以去原諒對方。我認為,原諒其實是避免戰爭發生的一個重要過程。但如果實際上,我的家人或者孩子被殺害了,我是否能夠做到原諒呢?這個問題我不太確定。能否抑制內心的憤怒?我不知道,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我希望能夠深入思考這些問題,並且讓我們未來如何看待這些問題變得更清晰,所以我非常希望能夠探索這樣的主題並進行創作。
ー平常在生活中,當你自己感受到憤怒時,會如何去抑制它呢?
與以前相比,我現在已經不太容易生氣了,雖然過去常發怒,但現在憤怒的情況少了很多。不過,當我真的非常生氣時,不會刻意去壓抑自己。我覺得發怒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雖然它是一種負面的情緒,但有時它也可以轉化為行動的力量。所以,我其實很珍惜這些情緒。比如,我一直很關心政治問題,但我認為日本是一個政治運作相對緩慢的國家,有時會困惑為什麼日本人似乎缺乏將憤怒轉化為行動的能量?我曾經也因為這樣的困惑,做過一些藝術展覽來表達這種情緒。所以在某種意義上,我會認為這些情緒對我來說是重要的。
ー許多人會認為負面情緒創作出來的作品是比較具有能量的,甚至最終能帶來積極的影響,對此是如何看待的?
當然,並不是所有作品都是由悲傷或悲劇所創造的,但我認為確實有這樣的情況存在。比如,我拍過一部紀錄片,探討時尚和環境問題。影片中有一位服裝設計師,他的衣服最終成為垃圾,並且堆積在非洲肯亞的垃圾山上。這種極端的負面元素,反而能激發作品的力量。這樣的強烈對比確實能夠為作品增添深度,不過最終還是要看你如何處理這些情緒。
ー請向台灣的粉絲們說一些話吧。
我不太確定在台灣是否有我的粉絲,不過昨天在導演講堂上有些人說有收藏我最初的作品,;還有,我之前曾為 The fin. 拍攝 MV ,這團也來台演出過,所以也有粉絲特地告訴我這些事。對於這些事情,我真的覺得大家看得很仔細認真,非常高興也非常感謝。真的謝謝大家。
延伸閱讀:《難言之隱》金馬影展台灣首映 資深男星奧田瑛二如何演活失智老人?
ーThe fin. 經常在海外活動,之前來台演出時引起高度討論,尤其導演拍攝的〈Night Time〉、〈Shedding〉等 MV 同時也獲得很不錯的評價。
The fin. 對於海外活動有強烈意識,我自己也比較偏向這樣的類型,所以和他們能有某種程度的共鳴吧。
ー導演也是希望能夠以海外為重心活動是嗎?
我希望盡可能地針對整個世界來拍攝電影。我年輕時想了很多,有人曾邀請我搬到倫敦或去洛杉磯工作,但回過頭來想,當我創作的時候,我覺得自己的根源非常重要。身為日本人這件事,我覺得是無法抹去、丟棄的。我反而覺得,如果不努力去珍惜這一點,可能就無法創作出真正深刻的作品。因此,我想要珍視作為日本人的這個根基,然後在這個基礎上,去跟全世界的人進行交流和溝通。
ー也就是越在地越全球的意思。
是的。關於全球化,特別是以藝術形式進行表達時,不可避免地會面臨這樣的問題,即使我用英語進行交流,是否就能真正理解英語的深層含義呢?我們並不是在同一個文化背景下成長的,也沒有一起看過同樣的電視節目,因此在文化上總是會有一定的侷限。所以我認為,應該要珍惜自己的母語或者是在那個文化環境中成長所帶來的深度,這樣才能創作出更加深刻的作品。

文:迷迷音
照片:迷迷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