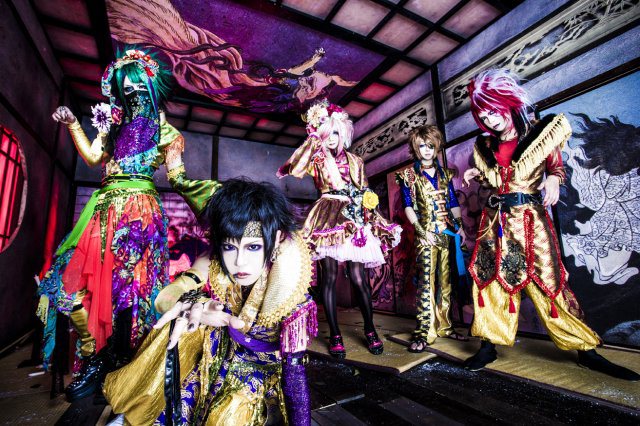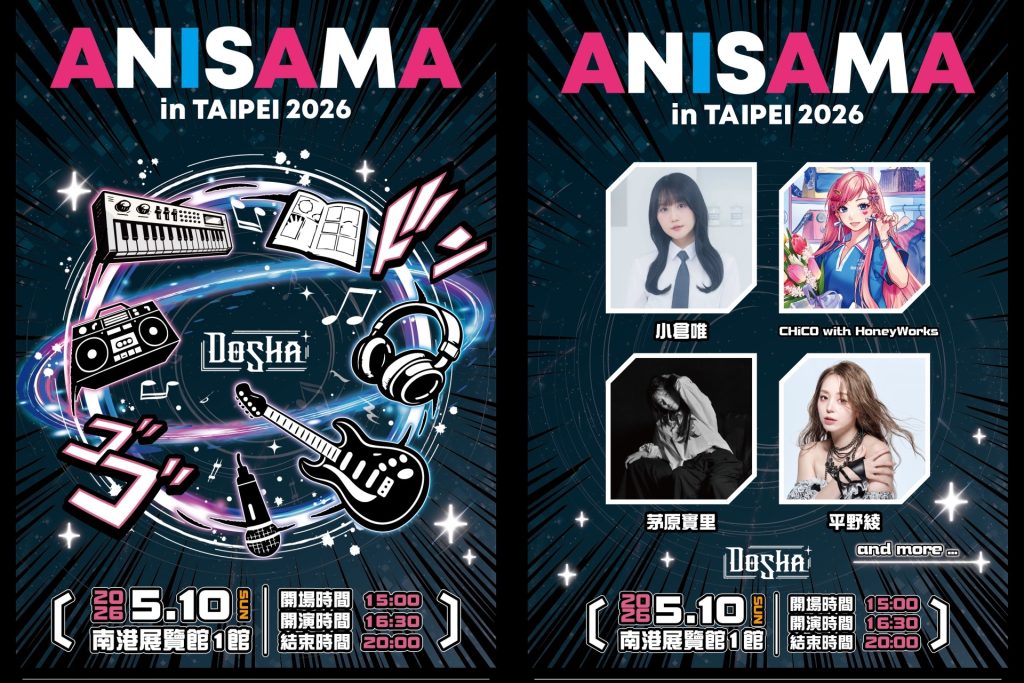─不順著主題來寫歌可以算是某種反抗的意味嗎?
下岡:幫忙設計專輯封面的設計師有寫信說道「我認為要從上而下地由樂團將訊息傳達給樂迷很困難」。我說「擁有能適時反抗的能力在這個世代不是很重要嗎?」。我雖然沒辦法將那種感覺用言語表達,但在作曲的同時感覺和自己潛在的想法一致。
─特別是下崗的樂曲,不論是音樂或言語都比以往更簡約,感覺能喚起聽者想像力的留白、空間、深度非常廣。會這麼想是覺得應該有人能理解下崗充滿社會訊息的樂曲,也應該有人能捕捉到些許下岡內心的想法,如果有人覺得空虛那也會有人得到救贖。總之曲風就好像要將現在樂迷所想的呈現出來,正因此我覺得每一位樂迷都能接受貼近現實的曲子。
下岡:我自己覺得若是能有讓樂迷產生某種誘因的歌詞就好了。不過那相當困難。正因此如果我寫的歌詞對樂迷而言能發揮那樣的功能,那會是非常開心的事情。
─我覺得Yogee的歌詞也富含許多想像空間,角館覺得那種感覺如何?
下岡:想聽!
角館:最近我剛好注意到減法的部分。比起像考題「請填空」般的空白,我覺得更能讓樂迷自由地聽那首歌。因此歌詞不要有太完整的故事性比較能和樂迷保持輕鬆自在的關係。至今為止都能無意間寫出留有那樣空白的曲子。不過最近似乎有點習慣性地將歌詞寫得太具體。
─是因為有想用歌曲表達、傳遞的事情嗎?
角館:或許是這樣。現在寫的新曲似乎缺少了一點空間,所以感到有點煩躁。
下岡:很難取得平衡呢。我記得『PARAISO』(2014年Yogee New Waves發表的第一張專輯)就有很大的想像空間。雖然我覺得經過不知道幾年終於摸索出自己寫歌的方法,不過開始意識到要寫出有想像空間的歌詞反而就寫不出來了。
角館:嗯。為什麼變得無法順利寫出來了呢? 或許過度地加油添醋也是初期衝動的行為之一吧。下岡在填詞的同時有時也會覺得「不是這樣」嗎?
下岡:有啊有啊。因此最近不填詞了,因為不管是在紙上或筆電,只要填詞就會對所寫的歌詞感到困惑。所以決定儘可能在腦海中先描繪到最後一句的歌詞,當腦海中的歌詞完成時再開始試著寫出來。
角館:喔,原來如此,可以當作參考呢。
─看到“Walls”的歌詞讓我想起村上春樹獲頒『エルサレム賞(耶路撒冷文學獎)』時關於「牆壁與蛋」的演講。想到這個就覺得作家總是……。
下岡:喔,「應該站在蛋的立場」的演講對吧。
─嗯。「牆壁」是社會制度,而「蛋」是代表處於庶民社會的想法,如果說撞到牆壁就會粉碎,那作家就應該無時無刻站在蛋的立場創造故事。
角館:若是這樣,我覺得蛋不要碰到牆壁最好。
下岡:原來如此。
─很像角館會說的話。
下岡:角館很常看書嗎?
角館:我平常不怎麼看書喔。不過喜歡看音樂家的自傳,最近的話我正在看ラッパー的漢所寫的自傳『ヒップホップ・ドリーム(嘻哈・夢想)』和フィッシュマンズ的解說本之類的書。因為我非常喜歡表達出男性孤獨面的作品。
下岡:我第一次聽到「フィッシュマンズ唱出男性的孤獨」這樣的講法,很棒呢。這麼說來的確就是這種感覺。
角館:我覺得佐藤伸治的孤獨情緒濃厚地反映在フィッシュマンズ的曲子。其中有些雖然唱到「你和我正相愛著,但能深刻體會到寂寞般的情感流露。這點非常吸引我。
下岡:我也是在19歲的時候遇到了フィッシュマンズ,要是沒遇到那個樂團自己的音樂人生果真就會改變吧。欸,不過聽這樣的音樂對19歲的我來說是超出能力範圍就是了聽。
角館:啊,或許我也是這樣吧。
─我覺得角館現在對1990年代的文化真的抱持著很大的興趣呢,角館覺得如何呢?
角館:最近被90年代的文化吸引,想知道那是怎樣的感覺。以前的認知大概就只覺得「似乎有那樣的文化呢」,大人們都說現在的我們試圖創造的文化氣氛和當時被叫做涉谷系的社會風氣很像。被這麼說之後就更想知道當時的事情,於是開始聽小澤健二、Flipper’s Guitar的歌。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