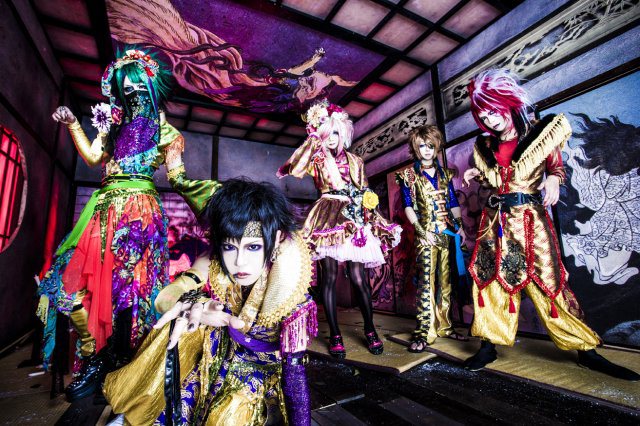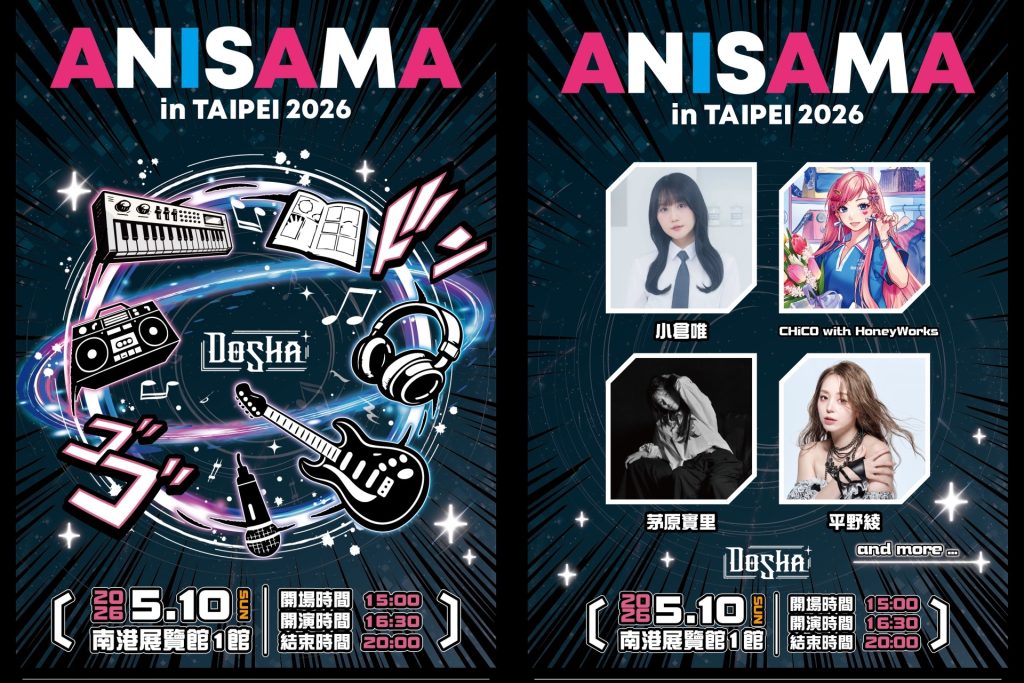有多少人知道MONO這個樂團呢?花了17年成為海外最多人聽的日本樂團。但在海外和在日本的知名度卻有著顯著的差異。
2000年MONO離開日本,開始在美國活動。在充滿絕望的紐約舉辦的第一次LIVE,拯救MONO的團員的一句話,一年超過150場如怒濤般地巡迴。在SNS、網路尚未普及的時代,MONO是如何發現那樣的地方?
這次的『SYNCHRONICITY’16 – After Hours -』聚焦在以海外活動為主軸的MONO,以一系列的訪談來剖析他們的成長過程。
雖然很不安,但非做不可的使命感更加強烈。
麻生:
首先先請教後藤。在1999年MONO誕生前是過著怎樣的生活(高中時期、MONO以前)?
後藤:
我是島根縣出雲市出身的。因為沒有Livehouse,在咖啡廳集合,從高一開始自己做錄音帶來賣。照明設備什麼的都沒有,全部都要自己做,用版畫印刷做入場券,最後聚集了約一千人左右。出了精選輯,也辦巡迴,就這樣在高中時期做了獨立搖滾。
當時也開始和廣島的樂團交流,於是就和廣島的那個樂團一起到東京發展。那之後就以主流出道,也做了很多不想做的工作,開始質疑到底何謂專業。回應對方的要求就叫專業嗎?若這就是專業,那我不當專業也可以。於是我決定絕對不要再和專業的人玩樂團。花了三個月,找練習室張貼的文宣、音樂雜誌之類的瘋狂打電話,最後就誕生了MONO。
麻生:
團員們是用應徵的方式產生的嗎?
後藤:
不,團員沒有一個是透過應徵的方式選出來的(笑)。結果都是透過朋友介紹,繞來繞去才有現在的成員。當時只有兩個選擇,一個是做不喜歡做的事,但能靠音樂吃飯,另一個選擇是做自己想做的音樂,就算不足以溫飽也沒關係。
我吃不飽、無法泡澡,只住四疊半的榻榻米都沒關係。但我決定剩下的人生要做自己喜歡的音樂,因此從那時候開始了MONO。那是很可怕的事情,但我已經有所覺悟了。1999年底決定了MONO的成員,在2000年就出發去美國紐約。

麻生:
活動地點不選日本而是海外?在召集團員前就已經決定要去海外發展了嗎?
後藤:
對,那也是大前提。我是為了在海外發展所以才在日本組樂團。
麻生:
不過當時沒有先例,網路又不發達。我想遠比現在還要艱難。是如何開始活動的呢?
後藤:
我在海外有一些朋友,當時大概就用傳真和寄信。我現在在玩這樣的樂團,如果方便能協助我辦LIVE嗎?於是我在六本木買寫有唱片公司和售票窗口的書,寫信給唱片公司,還寄了為數可觀的Demo過去。總之我既不會講英文,又不知道怎樣才能在海外生存,怎樣才能在全球發行自己的CD,怎樣才能辦巡迴,但也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做下去。不過或許比從出雲到東京還簡單呢。
麻生:
真的很獨立呢。比從出雲來東京還要簡單的理由是?
後藤:
在沒有Livehouse也沒有錄音室的地方自製錄音,還聚集了一千人,比起像這樣全靠自己的力量完成來得簡單多了。之後在東京出道、變成職業音樂家,還到全日本巡迴,都是以前做過的事情。這麼比起來從日本到紐約就不是什麼難事了。畢竟也有一些東西是只有美國才會接受的。
麻生:
但沒經過深思熟慮就直接去國外不會覺得很不安嗎?
後藤:
嗯,當然會覺得不安,想著如果這樣不行的話會變成怎樣,但非做不可的使命感更加強烈。從組成樂團後也跟團員說我們就是要在海外活動的樂團。不過結成當時有團員還沒有護照就是了(笑)。MONO今年是第17年,和專不專業無關,大家從頭開始一起累積經驗、一起看同樣的東西、一同感受、彼此互助,全員都站在同一條線上,於是才有今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sHC-O1BPCM%20
因為有那句話才有現在的MONO。
麻生:
雖然說要去海外發展,但是第一次出國,真的好厲害(笑)。去紐約的生活如何?
後藤:
糟糕透頂!我們把樂器、踏板之類,能賣的東西都賣了,東拼西湊才有旅費去紐約。然後我們第一次的演出是在曼哈頓一個叫Mercury Lounge的場地。我們比主要樂團早很多開演,但台下觀眾只有五個人。我們把能賣的東西都賣掉,籌到幾十萬終於能在紐約追求夢想,但觀眾卻只有五個人!那真的非常心酸。
然後在那五個人面前演出了45分鐘後,團員們一起去吃飯,大家吃很多呢(笑)。不過我只擔心之後該怎麼辦,連湯都喝不下,一心想著已經沒有能變賣的東西了,也無法回頭,該怎麼辦才好?。雖然想說去了紐約或許會有所改變,但現實十分慘烈。

麻生:
不過即使如此MONO還是沒有回到日本,而是跨過障礙。我想那是很難忘的事情,是怎麼脫離困境的呢?
後藤:
我們第一次的LIVE結束後住在蘇荷的飯店。團員們一起在陽台聊天,我說大家跟著我紐約,但第一次的LIVE卻只有這樣的人數,真的很抱歉。結果團員們說「難免的啦,就算在大阪五個人還是五個人對吧。因為沒有人認識我們阿。」還說「只能繼續做下去不是嗎?」。那真的很重要,正因為有那幾句話才有現在的MONO。
而後那樣的生活果真沒有持續很久。送CD、收到來自各方的信,不久就和約翰佐恩創辦名為Tzadik的唱片公司簽約。接著就發行了全球性的第一張專輯《Under The Pipal Tree》,後來漸漸有些來看LIVE的人會說要協助我們辦LIVE,接受好多幫助。從那之後就有如怒濤般的累積很多巡迴的經驗,甚至只能在車上睡覺。

每一場LIVE都是死命的演出。我們就連在演出中弦斷掉都很討厭,處於非常緊繃的狀態。
麻生:
那樣的想法和行動力、信賴關係真的好厲害。在那之中有什麼印象深刻的趣事或具體的經驗嗎?
後藤:
我們收到來自各方的援助,像是Jim O’Rourke在紐約和我們一起演出,還給我們一半的報酬金,真的很感謝。即使是現在也有跟Jim O’Rourke借錢呢。此外以紐約為首,很多美國人來看我們的LIVE,受到各式各樣的幫助。如此一來,每辦一次LIVE動員人數就增加,進而獲得更多人的支持。真的是接二連三的奇蹟。也有很多關於搖滾越的經驗呢。在車上補眠的巡迴、住在五星級飯店,累積了各式各樣的經驗。
麻生:
在美國做過這些事的日本人有多少呢。真的非比尋常呢。在美國是抱持著怎樣的心情,又是怎麼讓自己廣為人知的呢?
後藤:
所謂主軸的樂團在休息室有水果、也有水有酒,會幫你準備各式各樣的東西。但之後的樂團就只有水。而像我們這種開場的樂團連休息室都沒有。但我們懷有夢想。那是講求實力的社會。在美國的樂團為數眾多,有如滿天星斗。而我們雖然也在裡面,但主軸樂團的團名字非常大,之後的樂團名字寫得比較小,我們的名字則是小到都快看不到了(笑)。不過我們一直想像著自己的團名會變得跟主軸樂團一樣大,我們的目標是在休息室中受到主軸樂團的待遇。
但剛開始時沒有像現在的巡迴策劃人,只能靠我們四個人來完成。因此每一場LIVE都拚死拚活得在演出。我們就連在演出中弦斷掉都很討厭,處於非常緊繃的狀態。因為從日本來就不能輕易回去了。不過辦一場好的LIVE就能延續到下一場,我們這樣一路走來也很幸福。在美國如果做出成績的話是真的會帶來下一次機會的。動員人數明顯增加,評價也很好。

麻生:
當時明明沒有網路,是怎麼讓風評廣為人知的呢?
後藤:
因為我們真的辦了為數可觀的LIVE。連續七個月都在辦LIVE的狀態。在我們的網頁有一個巡迴的頁面,是依照年份分類的,從1月到12月幾乎無間斷,看得都起雞皮疙瘩了呢(http://www.monoofjapan.com/jp/tour.php)。沒想到這就是自己的人生之旅呢。上了年紀得現在有些事情在體力上已經做不到,但在每個當下都會用盡全力去完成。
讓耳朵爆炸般的體驗、與電影並駕齊驅充滿戲劇化,及滿富情感的無聲電影,不分音樂類型,就是想做出像這樣具獨創性的音樂。
麻生:
透過這些活動,MONO在全球也被賦予Post-rock這個特別的定位。我覺得充滿獨創性MONO的音樂是不止於Post-rock,而是具有MONO獨一無二的世界觀。對於被定位成Post-rock這件事後藤有什麼想法?
後藤:
在Post-rock這個音樂類型問世前,在肯德基州路易維爾就已經有很厲害的樂團叫「Slinnt」,堪稱是Post-rock的前身。正因為有他們,所以後來才有受他們影響的英國樂團「魔怪」、加拿大的Godspeed You! Black Emperor、美國的天空爆炸、冰島的席格若斯。那麼在亞州最有名的器樂團是誰?於是就變成MONO了。
與其說是Post-rock,不如說是各國偏重樂器的樂團。有人看到這樣的器樂團就創了Post-rock的音樂類型,這和巴哈、貝多芬、莫札特被歸為同類是一樣的,每個國家每個音樂家都有自己的風格。
麻生:
或許當時的確流行將具個性化的器樂團稱為Post-rock呢。
後藤:
嗯,真的是這樣。話題可能有點偏掉,但當流行Grunge的時候,有Nirvana、珍珠果醬樂團之類的樂團,可是Grunge卻只風靡了三年半左右。而我們開始活動到現在經過好多年,沒想到會有Post-rock熱潮,當時就在想完蛋了,搞不好會和Grunge一樣,三年半後就消失了。因此2003年左右我對Post-rock就是有種無法繼續下去的認知。

麻生:
對音樂類型和熱潮具有危機感的意思嗎?
後藤:
嗯,對阿。當時Post-rock從沒沒無聞到突然變成音樂主流,於是開始從中思考如何應對。当時有Tortoise之類的樂團,慢慢的進化到可細分成融合舞蹈的,也有大眾化的Post-rock。而我則是在想作曲時不從安靜變吵雜就是創新,以吵雜作為開頭就是新型態。大家都很煩惱呢。
但明明具強硬風格、嶄新的音樂在當時被稱為Post-rock,但當表現出嶄新的一面時,卻變成嶄新的普通音樂了(笑)、陷入嶄新的迴圈,開始思考在這樣的形式中要怎樣做出新的音樂,結果就變成頭重腳輕的音樂。看著這樣的現象就覺得好像哪裡不對勁。
麻生:
嶄新的普通音樂真是個好的形容(笑)。但我懂這個意思。
後藤:
結果我們的音樂到底是什麼,經過了17年……。有人認為金屬是表達內心的哭泣、Hardcore是嘶吼叫喊、龐克是生存的方式,將每個要素和身分一起納入,思考音樂到底是什麼,所得到的答案並非被音樂追著跑,重要的是生活方式本身的獨創性,別人的事情跟自己無關,而是自己最初的心情及感受,『無論如何就是想做這樣的音樂』。
2003〜2004年左右我抱持著只要是自己相信的音樂就是好的想法。因此已經跟音樂類型無關,就聲音來說,想做出讓耳朵爆炸般的體驗、與電影並駕齊驅,充滿戲劇化、情感的音樂已經不分音樂類型,就是想做出獨創性。
麻生:
我覺得MONO的確是完完全全的獨創音樂。不過我覺得在某些地方還是感覺到日本的要素存在。在向全球傳遞音樂的同時,有意識到想做出日本的感覺嗎?
後藤:
是阿。從背景來說,MONO的音樂就只存在於MONO。例如在英國演奏MONO的音樂時,可能會有像日本優柔寡斷的感覺。因為在英國、美國都會有自己國家不必要的東西,因而追求那些沒有的東西。那是無意識的,並非特意說要穿和服、演奏古代宮廷樂之類的,但曲子本身卻應該已包含這些成分。這是在日本成長的過程自然而然就會得到的產物。若要做自己喜歡的音樂,就真的會變成一個日本人做出來的音樂。能不能讓自己有所共鳴非常重要。我們一路走來都貫徹著這樣的想法。
文章來源:https://synchronicity.tv/interview/946/
翻譯:迷迷音
相關文章:「MONO所描繪的新音樂節 透過『After Hours』想傳達的東西」 MONO訪談翻譯(二)